人生就是在一條隧道裡,進行一場陰錯陽差的表演——蘿荷.普羅沃絲特(Laure Prouvost)與她的異想世界
文 / 江凌青

Laure Prouvost
我告訴這群孩子,「這個下午,你們要扮演我的祖父的孫子,我的祖父在隧道裡迷了路,這是件很悲傷的事」;這群孩子們問我:「所以,我們必須以別人的身體出現嗎?」我回答:「沒錯,正是如此,就這麼做吧!」
I told these kids: “This afternoon you are going to be the grandchildren of my grandfather who is lost in a tunnel and it’s very sad,” and they asked, “Do we have to be in someone else’s body?” I said, “Yes, exactly—do that!” 蘿荷‧普羅沃絲特1
異鄉之為家
蘿荷‧普羅沃絲特(Laure Prouvost, 1975-)是位在倫敦定居超過15年的法國藝術家,或許正是因為她長期遠離家鄉的緣故,反而使得她的作品中總是充滿了關於家庭、身世的想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莫過於她在多件作品中都陸續提過的那位「在位於英國湖區的家裡挖了條通往非洲的地道之後,就再也沒有回來的爺爺。」2而她的作品中,也總是充滿了流露出濃厚家庭生活氣息的日常物件或食材,只是這些素材到了她手中,總像是踉蹡了一步變了形,於是活魚成為帽子,啤酒瓶和熟爛的水果一起成為雕塑,指縫之間成為觀景窗。
從學經歷背景來看,普羅沃絲特是一個非常標準的、以動態影像藝術為媒材的藝術家。她在18歲來到英國,先後就讀於聖馬丁與金匠藝術學院,主修的科目一直都是「影像與錄像」(film and video),也遵循著英國藝術體制的正軌往上爬,先後在泰德英國美術館專門展出英國新秀藝術家的「Art Now Lightbox」、Frieze藝術博覽會展出,並且成為英國最大的動態影像藝術機構LUX培育的重點藝術家,也陸續獲得了具有指標性意義的麥克斯瑪拉女性藝術獎 (MaxMara Art Prize for Women, 2011)和泰納藝術獎(Turner Prize, 2013)。除此之外,她也是錄像藝術資料庫網站tank.tv的總監。
近年來,她的作品多是由藝術機構委託並提供充足資金的成果,例如2011年她獲得一個專門支持藝術家拍攝影像作品的機構「Film London Artists’ Moving Image Network」 (FLAMIN)的資助,首次與一整個攝影團隊完成劇情長片《晃遊者》(The Wanderer, 2011);2012 年,又在麥克斯瑪拉女性藝術獎的資助之下,以駐村六個月的時間與倫敦白教堂藝廊合作完成錄像裝置《吞嚥》(Swallow, 2013);而讓她獲得泰納獎的作品《還要茶嗎?》(Wantee, 2013),則是泰德英國美術館(Tate Britain)與英國湖區的藝術機構Grizedale Arts共同委託,為長居湖區的德裔藝術家庫爾特‧施維斯特(Kurt Schwitters)回顧展創作一件回應施維斯特之生命史的作品。
從上述的資歷來看,英國顯然已經成為這位異鄉客真正的家;或者說,英國藝術圈完全接納了這位異鄉客(她是泰納獎史上,首位獲獎的外國藝術家)。從表面看來,她完美地嵌進了當地的藝術圈,而她在學歷、獲獎、獎助、駐村、藝術博覽會等各方面的經驗,合起來簡直就是一部在英國藝術圈的《發達典範》。
打開客廳地板底下的隧道入口
但是,如果你在Google上搜尋Laure Prouvost、點入她的官方網站之後,所有關於「發達」、「典範」的定義,就會不斷在你眼前糊開,像是一張以水性墨水筆寫了寥寥數筆的紙條,在雨中軟爛成藍色的泥濘。
好的,你現在大概已經來到了http://www.laureprouvost.com/;也看見了在全白頁面中的一小片藍色海景,如果你的電腦有下載開啓這個網頁所需的程式,你大概也已經聽見了那刺耳的、瓷器在地上摔破的噪音。現在,點下那枚藍色海景圖。
你會看到一個對於當代藝術界來說,陽春得令人感到困窘的網頁。網頁上寫著「請幫助我們募集資金,為爺爺建造一座遊客中心,在他(未來會從隧道)出來的地方」,上面零星擺了幾張照片,有的是遊客中心設計圖、內部房間的想像圖、甚至還有一條「可以讓茶流入湖泊或海洋的滑水道」(tea slide);網頁下方,展示了一張普羅沃絲特本人在2013年泰納獎的頒獎典禮上領獎時,配戴的她自己設計的絲巾(更精確來說,是英國人用來擦拭餐具的「茶巾」),下方寫著「你也可以擁有!就和電視上看到的一樣」、「來我們的EBAY商店上購買這款茶巾」。


Laure Prouvost, Layout of the artist's website
眼前種種的資訊碎片,諸如:為迷路的爺爺建造遊客中心、滑「茶」道、買一款藝術家在泰納獎頒獎典禮上使用的配件等等,都暗示著一件事:這位藝術家並不想把自己或自己的網站「裝潢」、「粉刷」得很厲害、很深奧、很有質感、或者,「很高級」。相反的,她好像打算在一開始就把花草壁紙撕下、然後把壁紙後面的水痕、窟窿、迷你而頑皮的塗鴉,獻寶一般地,秀給你看,然後煞有介事地描繪一個明顯是虛構的訊息。
影像是一種活物式的機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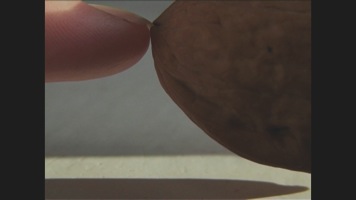
It, Heat, Hit, 2010
6 minutes Colour, Stereo
在普羅沃絲特的網站中那種強烈的戲謔、調皮與試圖對於既有的藝術體制開玩笑的態度(例如把泰納獎頒獎典禮當作置入性行銷) ,在她的作品中,則以「何為影像」這個問題出發點。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普羅沃絲特從來都不掩飾「錄像藝術令人不耐煩」這件事情,甚至樂於以坦承面對觀者的焦躁的方式,來編輯影像。在這次台北雙年展展出的作品〈它、熱、擊〉,不但每隔一分鐘就提醒觀者們「這部影片還剩幾分鐘」,並且在片頭就提醒觀眾「觀影守則」,例如:
這件長約6分鐘的影片需要你全神貫注,所有在Part 1出現的細節,對於Part 2都非常重要。
This 6 minute film requires all your attention, each detail of Part 1 will be essential to Part 2.
這部影片裡的角色們都很高興你在此加入他們,他們會竭盡所能來吸引你的注意。他們渴望你的參與。
The characters in the film are glad you’re here to join them. They would do anything to get your attention. They’re desperate for you to engage.
上述句子不斷突顯了影像做為一種時間藝術的結構,甚至將之視為一種以時間-空間結構(temporal-spatial structure)存在的活物,也因此可能與正在觀看影像的人們,產生有機的連結。
普羅沃絲特配置字卡、旁白與影像的方式,也透露了她不只將影像作為一種再現或呈現的媒介,而是一個能即時對影像內容做出回應的「機關」。例如:
- 在一位面露憤怒的男子的畫面上,字卡呈現了「在他的憤怒之中,影像都在焚燒」(In his anger images were burning)。
- 在「影片必須在這裡轉折」(The film has to turn here)的字卡之後,出現的是她以手持攝影機拍攝一台轎車緊急轉向的畫面。
- 在一片滿是綠藻的池塘水面的畫面之後,則出現「溺水、吞嚥這段文字」(Drowning, swallowing the text)的字卡。
上述這些簡顯易懂但卻不具特定敘事意義、甚至不符合邏輯(例如畫面中的男子生氣到讓影像都燒起來了)的連結,在普羅沃絲特的作品中反覆出現。但這種形式的微型詼諧,不也散佈於多數人的日常生活當中(那種突發奇想的小玩笑、冷笑話),甚至讓生活突現光芒嗎?
在我看來,普羅沃絲特相信這些微型情感能成為藝術,而創作這樣的作品,就是將那個與當代藝術領域失聯已久的抒情傳統,重新拉回語言的行動。
不精準也可以是人生的選項
2011年的長片《晃遊者》進一步挑戰文字與影像之間聲氣相通、甚至黏著牽絲的關係。這部影片的劇本,是根據另一位藝術家羅里‧麥克白(Rory Macbeth) 翻譯的卡夫卡《變形記》。這個版本的特殊之處在於,麥克白不但不懂德文,在翻譯期間也並未使用任何字典,僅仰賴個人直覺與誤讀。
《變形記》裡描述主角 一覺醒來變成怪蟲的開場片段:
有天早晨,推銷員Gregor Samsa 歷經一場不安的夢醒來後,發現自己變成了一隻巨大的怪蟲
When Gregor Samsa woke up one morning from unsettling dreams, he found himself changed in his bed into a monstrous vermin.
在麥克白筆下變成了:
當Gregor Samsa在Morgens與Traumen之間衣冠不整地遊蕩時,仍舊感受到他從Bett開始就出現的心神渙散與噁心狀態,最後他意外來到Ungeziefer。
As Gregor Samsa wandered disheveled from Morgens to Traumen, distracted and sick since reaching Bett, he came unexpectedly to Ungeziefer.
德文中的「早晨」(Morgens)、「夢」(Traumen)、「床」(Bett)等辭彙,在麥克白的翻譯中,全數變成地名。語言的類同與差異,在這個荒謬的翻譯計畫中,成為製造敘事的舵手。


The Wanderer, Betty/Drunk Sequence, 2012
HD video, 17 minutes 35 seconds Colour, Stereo
Installation view, International Project Space, Birmingham
普羅沃絲特的六段式影片,則將麥克白荒腔走板的誤讀,轉化為影像,甚至試圖讓影像內的世界直接與影像外的觀者溝通。例如在「喝醉的貝蒂」(Betty Drunk)這一段裡,從頭到尾不斷以爛醉形象出現的貝蒂,就一度對著鏡頭說:
你摸不到我,因為我他媽的只是個影像!
You can´t touch me, I am just a fucking image!
那樣悍然的態度與一針見血的陳述,讓觀者不得不注意到自身「窺伺者」的位置。作為一件以「誤讀」為基礎的作品,普羅沃絲特的影片提醒我們的是:在文字與影像中,真有什麼牢固不搖的現實、邏輯或真理嗎? 不精準是否也可以是一種選項?我們又為何需要執著於「精準」?(這對於來到美術館追求「標準答案」的關者來說,可以說是打了好大的一巴掌)「不精準」這種選項的存在,正是普羅沃絲特將理性化為抒情的要訣。
誤讀作為一種生命常態


Wantee, 2013
HD video, 15 minutes Colour, 16:9, Sound
普羅沃絲特融紀實元素、抒情自傳於一爐的《還要茶嗎?》,呈現了一間坐落於施維斯特(Kurt Schwitters)生前居住的英國湖區的小木屋。根據普羅沃絲特的說法,這間小木屋是她以觀念藝術家的身份與施維斯特結為好友的祖父的故居。普羅沃絲特在旁白中,描述著祖父母在此地的生活,她一邊拍攝、一邊觸碰屋內的物件,其中包括許多(宣稱)由施維斯特贈與、但卻被祖母拿來當作托盤、椅腳桌腳或肥皂盆的小型雕塑作品,言語間流露出對「藝術何用」的質疑。
在普羅沃絲特如同訴說祕密的低語聲中,也不時穿插了煮水壺運作的隆隆聲,以及藝術家高聲大喊「爺爺!」的尖叫聲,當她提及祖父「挖了條通往非洲的地道,就此失蹤」時,語調更是悲戚而神經質。
這一切是真的嗎?普羅沃絲特真的有一個觀念藝術家祖父嗎?小木屋裡的物件真的是施維斯特的作品嗎?

Wantee, 2013
HD video, 15 minutes Colour, 16:9, Sound
普羅沃絲特未曾透露祖父的名字,因此我們無從考證這位曾與施維斯特交情匪淺的觀念藝術家到底是誰。但影片中卻安插了許多關於施維斯特的史料,例如影片標題來自於施維斯特的生平,因為施維斯特的伴侶總是喜歡殷勤詢問客人「還要茶嗎?」(want tea?)久而久之施維斯特就直接喚她「Wantee」。為了配合這個典故,影片中也出現許多造型奇特的茶杯組,在裝盛紅茶配牛奶的畫面中,傳達出一種飽含手作質感而凹凸不平的家常氛圍。
另外,每當普羅沃絲特提及某項「被當作日常物件使用的藝術品」是出自施維斯特之手時,總是會穿插一張類似的作品圖片,暗示著「影片中提到的作品,確實存在於施維斯特的創作年表中」。
觀看普羅沃絲特的作品時,探究何者為真並不重要, 最重要的,其實還是我們從自己的世界向外看,看到了什麼。其實那個「什麼」,有很高比例是誤解與誤讀,但我們總是無法遏止這樣的不精準在生命中反覆發生。
但正是因為她對於這些「不精準」的認真,使得她看似破綻百出的影像成為一種貼近人生百態的必要抒情。她的作品一次又一次地提醒了我,人生不過就是一場陰錯陽差地展開之後(畢竟我們沒有人「計畫」自己要被生下)、直到死亡都不能中止的演出,而且在這整個過程中,我們常常都像是置身於一條黑暗而不知出口在哪的地道中,就像普羅沃絲特的爺爺一樣。
既然出不去、回不了、還沒到,不如就好好回應生命中諸多的不精準、誤讀與錯身而過吧——即使生命中總是有許多時刻,像是摔破的磁盤一樣,發出了哐啷的碎響 。
[1]:Jarrett Earnest, “Ideally This Interview Would Answer All of Your Questions: Laure Prouvost in conversation with Jarrett Earnest”, (2014.3.4), 2014.9.13檢索。
[2]:參考《衛報》與普羅沃絲特的訪談,Stuart Jeffries, “Turner prize winner Laure Prouvost: 'I'm very strange'”, (2013.12.3), 2014.9.13檢索。
參考網站
本文改寫自〈以誤解抒情:Laure Prouvost與她的影像藝術〉,發表於《Not Today》雜誌第2期,2014年春季號
All Images Courtesy the artist and Mot International


